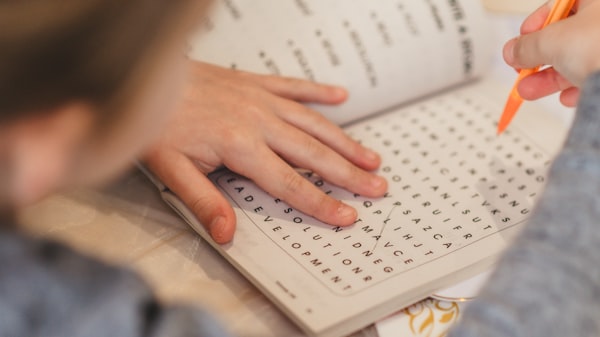- 欢迎使用千万蜘蛛池,网站外链优化,蜘蛛池引蜘蛛快速提高网站收录,收藏快捷键 CTRL + D
蜘蛛为什么要拉网才能活(蛛网丝的成因)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棵桑树驻守在我们部队大院的东北角,高出院墙,直径跟坦克炮管差不多。这不稀罕。稀罕的是它长在墙根的一堆乱石中,根须扎在石缝里,身子呈25度角旁逸斜出。
谁会这么种呢!野生的?风卷来的?抑或鸟儿衔来的?
想来它若有选择权,也不愿意在那干涸贫瘠又杂乱的地方守着我们吧?
年复一年,没见有人修剪和施肥,它竟也有了虬枝接叶而吟风的姿态。袅袅城边柳,青青陌上桑。布谷声起,初夏的风儿吹拂我们额头的时候,它满枝丫的桑葚跟着风儿微微颤动。没几天,桑葚透着光亮从青色到红色再到紫色,跟着来的,就是我们的采摘。
大院初生之犊和豆蔻年华的孩子集结起来能有一个加强排。那年桑葚红了的时候,我们自个儿整编了个“兵团”。小军打小就崇拜战斗英雄,写作文长大了干什么,他不是坦克兵司令就是独立团团长;他爱看《回忆与思考》《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》和《在柏林方向上》,看懂多少不知道,反正说起朱可夫,他滔滔不绝意气风发一时多少雄豪气。小军还是大院“三个火枪手”的首领,为这不管哪个孩子闯的祸,大人们总是唯小军是问,他那个当副师长的爹,也从来不问情报是否可靠,回回二话没有,抄起棍子就打、抡起皮带就抽。从小到大,小军替大院孩子挨的打一言难尽,他当“兵团”司令,个个服!
那天小军绕着桑树转了三圈,然后意味深长地盯着树根看了小半天,说:不屈不挠,它是勇敢者。
“勇敢者”就这么成了我们“兵团”的番号。一切行动听指挥,步调一致采桑葚,小军说这是“勇敢者”的第23条军规。采摘桑葚从此正规化,并成了我们院定的节日。
节日至少延续三天。列队,立正稍息报数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仪式。仪式之后小军一声令下,然后男孩飞檐走壁上树,女孩树下抻着脖子守望。这是我们采摘的排兵布阵。
云从树叶间过去,蚂蚁在树干上转圈,蜘蛛兴高采烈地拉网,花天牛更是气定神闲地吃了半张叶子……许是我们的笑声引得鸟儿飞来。鸟儿东啄一下西啄两下,忙得更叫一个欢。小军其实心软得很,他不让我们赶鸟儿,说没准就是它的爷爷把这棵桑树弄来的,饮水思源结草衔环,咱们得仗义。
鸟儿因此成了“勇敢者”兵团的“特种兵”,我们任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搞游击战。它不知道熟透了的桑葚轻轻一碰就能掉下来,那样的桑葚好吃得不得了。
我们酣战淋漓时,炊事班叔叔或者警卫员叔叔会在不远处观望,等到我们够不着攀不上哇哇乱叫时,他们会迅速出兵成为我们强大的外援。
采摘结束,我们就地吃桑葚。吃桑葚也有仪式。围坐一圈,先唱“真是乐死人”,然后不分,不抢,不闹,最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互相抹个大红大紫的脸蛋儿;吃够了,全体紫舌头,唱着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”,回家去。
三天里,我们天天这么血色浪漫到黄昏,即便口若血盆齿排铜板成了“吸血鬼”,即便我们把爹们的将校呢染成了绛紫色,大人们也不骂。为什么不骂呢?我们一直忘了问。
我们也忘了问,我们留在树上的桑葚,他们是什么时候做成了桑葚酒?
小军他们几个当兵离开大院的那天,喝的就是桑葚酒。他们走后,“勇敢者”兵团解散,大院开始寂寥。又一年桑葚红了的时候,我们几个散兵游勇孤单单地坐在高高的树丫上,听桑葚讲那过去的故事。(许平)
相关文章推荐
- 无相关信息